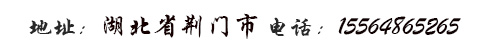推莫相逢了吧
|
北京哪家白癜风医院好 https://wapyyk.39.net/hospital/89ac7_labs.html 文/北雪摘/命里命外,春柳秋华,她还没想明白到底是幸还是不幸,就被时间推了一把,只能跌跌撞撞地接着活下去,甘不甘愿的,只当个糊涂人。图片来自网络 在白英还有一年就要出宫的当儿,皇帝驾崩,她伺候了好多年的娘娘也跟着去了,娘娘的大儿子登了基。她守着娘娘的宫殿,看着宫里新来的新人,使劲回想自己的当初,可还没想起来就被叫到了冷宫的一处破房里。 御前大总管指着床上满身是血,奄奄一息的男人对她只说了五个字:“好生照顾着。”说完转身便走。 她看着床上那人的脸,惊起一身冷汗,连忙跑出去拦住大总管,褪了手上的银镯急急地往他手上送,“恳请大总管指点,这人……是要怎样照顾?” 她这些年混得不错,娘娘待她极好,大总管也要给她几分薄面,可大总管将银镯又放回了她手里,面无表情地对她说:“陛下的命令,要你好生照顾,其他的杂家概不知晓。” 夜风吹过,激起她背后冷汗,透心的寒。 大总管见她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,走了几步,又转过身,到底不忍,提点了她一句:“你是在陛下面前服侍过的,陛下向来夸你谨慎体贴,这次陛下开金口偏偏要你照顾,还不明白吗?” 她恍然大悟,向大总管行礼,“多谢大总管提点,奴婢一定细心照顾……” 大总管急忙将她扶起,说:“从此以后,对于那个人,姑姑千万慎言。杂家不能逗留,姑姑在这里,也要……好自为之。” 这,毕竟是冷宫啊。 她在这宫里也算有年头了,更与他是旧相识,这句话里几分是卖人情,几分是真情流露,她依稀能分辨出。 他对她一时仁慈,既是仁慈,那便是她之处境让他也觉得惋惜了。 她心中有数,端端正正给他行一礼,他摆摆手匆匆走出了门,她对着门长礼,直到门缓缓关上,就像是她第一天来到这宫里,看着朱红色的大门在她身后静静关闭,锁她天真烂漫,锁她青春年华,可她那时满眼都是新事物,尚没有空余对它一礼行之。 她转身看向这间冷宫,荒僻得很,孤零零的一间小破屋四周却站满了侍卫,门口的那个递她一个药箱便再不多语。 这何尝不是另一扇门。 她缓了口气,提着药箱走进了房。 床上的男人没有声响,血却浸满了被褥。她扯开了被子,倒一口凉气。男人身上都是刀伤,皮肉翻出,惨不忍睹。她忙伏在他口鼻边,焦急地等待着,终于听见微弱的呼吸。 她忙跑了出去,狠狠敲门,门口的侍卫开了门,也将刀驾在了她脖子上。 她忍不住浑身一哆嗦,但还是强忍着害怕开口了,“大人,屋里的那人伤太重了,得叫太医,不然会死的呀!” “上面说不许让任何人进这个屋子,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,死了也不关你的事。” 她顿时心肺俱凉,讷讷地转了身,往回走。 床上那人呼吸更弱了。 她不信,忙翻药箱,竟真的在最后一层找到了一个吊命的药丸,连忙给他服下。不久,他铁青的脸色终于有了好转,她这才松了口气,开始给他清理伤口。 她用刀割走烂肉,敷上药粉,他皆一动不动,等都处理完了,换了衣服与被褥,到了夜间,还是发作了。 他浑身滚烫,高烧不退。 她没别的法子,只能出门,打冰冷的井水,沾湿了布巾擦拭他的身体,久碰冰水,她的手冰得麻木,索性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取暖,他因为难受而皱起来的眉头松弛开来,她看着觉得好笑,可刚笑一声,就笑落了泪。 娘娘走了,她曾经捧在手心里的小儿子便变成了这副模样,不知道娘娘知道了要多伤心。 到了后半夜,他开始呓语,一会儿凄厉地喊母妃,一会儿喃喃地唤皇上的名讳,她摸摸他的额头,他便会安静一会儿。她守他一整夜,不敢懈怠,万幸的是,烧终于是退了一些,只是人还没醒来。 她给他的伤口换了药,在他床头从天亮坐到天黑,人还是没醒。 她摸摸他的头,轻声地唤:“殿下,您这样赖床不起来,娘娘会担心的啊。” 他皱着眉头,头无意识地往她手心里拱。 她想起第一次见他时,是入宫的第二年。那天,娘娘心情很好,做了一盒子点心让她给五殿下送去。五殿下正在练武场,她到时,武场师傅在教导别的皇子,他许是听得烦了,等得倦了,一手握着枪,倚着枪蹲在地上,一脸的无聊,却又天真年少地看着周围。 见她来了,竟也认得她,张口便叫她“白姑娘。”欢欢喜喜地接过了食盒,可一想到他刚才那样子让她瞧了去,又不好意思地红了脸,放低了声音对她说,“我方才只是歇歇,白姑娘可别跟母妃告状我偷懒啊。” 她看着眼前这个遍体鳞伤的男人,竟拼凑不出一丝那个意气昂扬的少年的样子。 在她心灰意冷的第三天,他醒了,看她的第一眼便唤她“是你……白姑娘。” 她笑了,一瞬破了满脸僵硬的冰,牵得嘴角都隐隐作痛,但还是温柔地说道:“回殿下,是奴婢。” 她为了方便上药,也为了替他散高热,就没给他穿衣服,这会儿,她也是轻轻掀了被子给他清理伤口。他什么反应都没有,眼里是灰茫茫的一片,直直地看向床顶。 她知道,这叫绝望。 但她仍是什么都没说,她没劝他要好好活着,也没说她可以帮他怎样怎样,她换完了药,就出了屋子,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,看着远方的天,长长地出神。她在想她进宫的第一天是怎样的…… 不知不觉想到了晚上,她接了饭,给他喂完,自己吃完了剩下的,到院子里门边还了碗筷,回了屋子,伺候他梳洗后,她把除了床上的唯一一个薄被铺在了桌子上,她蜷蜷身子,躺在了桌子上。 马上要睡着了,他却突然开口唤她:“白英。” 她腾的一声坐了起来,刚想下地看他怎么了,他又接着说:“你为什么会来这儿?” 她老老实实地答:“回殿下,是陛下叫奴婢来的。” “叫你来做什么?” “好生照顾您。” 他沉默了许久,或许还有一声嗤笑,她没听真切。 可这下一句,她可听清了,“你知道我的一身伤是怎么来的吗,就是我的好兄长啊。” “他还是那么胆小,夺了皇位还怕坐不稳,想趁宫乱也杀了我。” 他越说越喘,声音里也带了癫狂,“他怕我也就罢了,竟也怕母妃,你知道母妃是怎么死的吗?” “殿下。”她打断了他,寂黑的夜传来几声破空的鸟鸣又归于寂静,她开口,是极清淡的语调,“殿下,您跟奴婢说这些做什么,奴婢也听不懂。” 他又沉默了回去,不再说话了。 白英躺了回去,侧着蜷身子,她按了按她胸口,胸口闷闷地疼,返上来一股酸意直冲鼻头。 她想起了那个温柔的女人,常常倚着门框对着夕阳,残阳若血,她高贵雍容,美若诗画。 她会在白英问是否太过偏爱五殿下时,不觉得冒犯而是笑着说:“老三老五我都喜欢,可喜欢是不可能一视同仁的,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有更喜欢。哎呀,小英儿还没成家,以后就会懂了。” 她不想懂了。 一觉起来,他竟又开始发烧,一个白天都不见好,晚上整个人打冷战,她把仅有的两床被子都盖在他身上,他仍冷的牙齿碰撞。 她跑出了门刚想敲门,夜风穿衣而过,让她清醒过来。 殿上的那个人或许根本就没想让他好好活着,自生自灭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。 她抹了把脸,又跑了回去,看着男人在床上颤抖唤冷的样子,一咬牙,把自己身上的衣服都脱了,钻进了被窝。 男人感觉到温暖无意识地凑过来,她避开他的伤口,轻轻地环住他清瘦的脊背。 她望着床顶,心里默默地祈祷,娘娘,您若在天有灵,庇佑他度过此劫吧。 她真的也要绝望了。 第二天起来他不再喊冷了,阳光照进来,脸有了血色,表情也安安静静,乖得像只蜷睡的猫儿。 只是他好像感受到了什么,手掌动了动,眼睛一动就要睁开。 她伸手捂住了他的双眼。 清晨的阳光温暖而缱绻,她看着他的脸,缓了声音,要用上所有的温柔,“殿下,您别睁眼,您没看见,就当没这回事,求您了殿下,您先别睁眼……”再也伪装不下去,她的声音渐渐开始颤抖。 他便一动不动了。 她起了身穿了衣服,走出房间时带上了门。 他睁开了眼,久久地盯着床顶。 床顶什么都没有,灰蒙蒙的,可阳光照了进去,添了丝暖意,让人恍惚觉得这是过日子的地方。 过了好一会儿,白英进屋给他送饭。他看着白英安静平和的面容,开口问道:“他把你送来照顾我,可有给你什么好处,我若走了……他又给了你什么出路?” 白英将饭菜一一摆开,面色未变,等收拾好了,抬起头看他,展颜一笑,“回殿下,奴婢能来照顾您,就是天大的福分了。陛下让奴婢好生照顾您,奴婢不敢懈怠。” 言下之意,便是什么都没给她。他缓过神来了,也是,一个奴婢,主子让她来她便来了,哪还能讨价还价。 那又是因何待他如此呢? 她给了回答,是皇上令她好生照顾他的。 真是个忠心的奴婢。 到了夜里,她又爬上那张窄小的桌子,他皱着眉,终于忍不住开口:“白英,过来睡吧。” 她诚惶诚恐地摇头,“殿下,这使不得的。” 他听得笑了,“这世上怕是再也没有五殿下了,你过来,我想看着你。” 他想起身给她挪地方,可她一步未动,垂着眼,“殿下,您如今无论是潜龙在渊还是日薄西山都是尊贵的五殿下,就如同奴婢,也一直都是奴婢。”她抬头直直地看向他,眼里似有温柔的笑意却又平静如湖不起涟漪,只是平淡地对他陈述,“尊卑有别啊。” 一句千钧,他再说不动一句轻巧的话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在他触手不可及的地方,背对着她,蜷缩而卧。这不是他一时慈悲就能跨过去的距离。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下去,他再没有像那样凶险的高热过,到底是从小就练武的大小伙子,将养着一个多月就能下地了,还能帮她浆洗衣服。她无奈地跟在他后面,把他晾得皱皱巴巴的衣服扯平,突然,久久不开的门被破开了,突然的,她都来不及收起脸上的温柔笑意。 明黄把一院凋零荒芜生生撕裂开来,新帝看着五殿下,嗤笑,”没想到你伤好得还挺快,都能下地了啊。“ 鞭声破空而起,尖叫着落下,又沉闷地结束,再起,再落,记不清多少个来回。 她跪在地上全身发抖不敢发出一点声音,而她细心养了一个月的殿下,此时正蜷着身子躺在地上,鞭子破开他的衣衫,血肉,伤疤,他整个人浸在血泊里,可一双眼却睁着,灰茫茫睁着,像是第一次醒来那时,快要溢出来的绝望。 她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五殿下,又一次碎了,如此轻易,怎么就如此轻易地可以毁了一个人呢…… 新帝挥舞着鞭子一次比一次狠,杀红了眼。 她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,在这宫里活这么多年,早就知道保己的最佳方法。 鞭声狠烈地划破冷宫这片小小的天空,她猛地起身趴在他身上,鞭子瞬间破开她的后背,痛得她扬起了脖子,叫嚎不出。 新帝红着眼,用鞭子指着她,“怎么,要给他陪葬吗?” 她急急地喘了几口气才发出声音,却不肯离开他的身体,只勉励撑着身子回答,“陛下恕罪,奴婢是陛下派来照顾的宫女,五……他旧伤未愈,这鞭子再受下去必死无疑。” 新帝挑眉,似乎这时候才有功夫打量他的好弟弟,他的好弟弟已经面无血色了。 哈,他笑了声,扔了鞭子,大摇大摆地走了,“老五,过两天我再来看你,你可一定得活着。” 她猛松了口气,疼得眼里哗哗地掉。 夜里没意外的,他又高热了起来,只是这回,他抱着她不肯撒手,像是说梦话般迷迷糊糊地说:“他,他得了皇位却还不肯放过我……” “母妃,母妃她用她的命换了我的命……白英,母妃她,她就死在我面前,白英,白英……”他泣不成声。 白英抱着他,早已经泪流满面。 而他还在呓语,一会儿母妃,一会儿新帝,说着说着,声音减弱,连眼里都是灰败一片。 她用力抱起他的脑袋,与自己的贴在一起,流不尽的眼泪沾湿了他的脸庞。 寂静的夜里,只有她一个人的自言自语:“殿下,其实那回奴婢给您送点心,路上没忍住嘴馋,偷吃了一块。后来看您挺喜欢那盒点心,都没吃够,奴婢愧疚了好久。” “殿下,其实奴婢挺希望您能撑过来的,您那么多回都撑过来了,这回也撑一撑好不好。奴婢其实偷偷跟娘娘学了做点心,等您好了,奴婢把当年欠您的还您好不好……” 怀里的人突然动了动,脸蹭了蹭她的脸,“好……” 她颤抖着身子,终于泣不成声。 隔了两天,外面突然来了人把床上的五殿下抬了出去,没给一句音信。 他被放在椅子上,浑身的伤痛让他连动弹一下都不能。奴才们给他梳洗,收拾出一个王爷的模样,放在大殿里。他看着皇帝和正走进来的镇南王,突然明白了皇帝欲让他死却仍留他一命的原因。 镇南王是他们的外公,曾当着母亲的面说过三子心思不正,不可为君,尤喜五子。老三想要镇南王手里的兵权,却又怕不成功,便叫上他这个傀儡。 他险些要仰天大笑,把镇南王召进宫,这样的破绽,老三啊老三,你还是太贪。 镇南王本就不信老三,加之老五给他递信儿,大殿会事散了之后就把老五救了下来,再仔细一问,当即怒火冲天。 白英一个人呆在冷宫里两月有余,不见他归,也不知外面早已变天。 只是那天她坐在台阶上,望着夕阳,望着望着他便披着霞光回来了,笑容如昨,拥她入怀。 她心里就有了数。 他和她并肩坐在台阶上,笑着问她:“现在咱能出去了,想做些什么?” 她答:“今年,奴婢就能出宫了,想早点出宫。” 他的声音沉了下来,可笑容不变,“宫外可是有家人在等?” 她眉眼含笑,“有的,一家四口。进宫那天,奴婢的母亲告诉奴婢,给奴婢说了件婚事,等奴婢出宫便能嫁过去。” 他离开她的那些天里,她每天都坐在台阶上看天,终于想起了她进宫那天的情景,母亲拽着她的手满眼泪水地说:“从此以后,家里便顾不上你了,你好生照顾自己。福子……福子来信说,他等不了你,我的娃怎么这么命苦……”说着又哭了起来。 入宫两年后,邻居来信,说她家着了大火,谁也没能逃出去。她的家彻底没了。 自那以后,她便有意地忘了这件事。人在宫里,日日如履薄冰,她得存个念头才能活下去,就这样,她骗过了她自己,而今也要来骗他。 五殿下听着,眼睛暗淡深沉,脸上还是笑着,“好啊,到时候我送你走。” 到了那天,他还真的来了,放下一堆国事,一身便装送她至门口。 她走过高高的宫门,抬眼看向外面的天,只看了一眼,就被人狠狠抱住。 那人狠咬她的脖颈,恨恨地说道:“你还真敢骗我!朕早就查过了,宫外哪还有人等你!” 她却像是突然疯了,不念什么尊卑了,拼命扭着身子,不管不顾地推打他,像是一条临死前折腾的鱼。 他一把将她背起,一路背回了寝殿,把她放在了寝殿的床上。 他附身吻她时还算温柔,可她却泪流满面,摇着头推拒他,嘴里是绝望的声音,“殿下,您别这么对奴婢,奴婢欠您什么呢,奴婢什么都不欠您的……” 她什么都不欠他的。 练武场上少年倚枪,从此她的视线总避免不了追随他。不过偷吃了一块点心,作何自责那么多年,无非是若除了这个,就再没什么可惦念的了。她本不该肖想,可那如金如玉般的人物躺在她面前,奄奄一息,她平静了许多年的心终于还是撕裂了。 她该谢谢三殿下的那句“好生照顾着”,遮掩了她的狼子野心,让他不会因为自己那难以自抑的欢喜而被吓走。 从来都是他欠她,他夺走了她的世界最绚丽的色彩,却毫无知觉地要来问她,作何待他如此…… 他吻了她的泪,“白英,我都知道。” 哪里有那么傻傻忠心的宫女,会抱着重伤的他哭泣不止,他一直都知道她喜欢他,只是那时的他活了今天没明天,没法回应。 他蹭蹭她的脸,“白英,我本想放你走的,可我自从答应了放你走,我就老做一个梦,梦见我走在桥上,你迎面走来,我想与你说话,你却把头转过去不肯理我。我上前拉住你,你却说我们的路不同,不该认识。” “我想起你跟我说我们尊卑有别,我每次醒来都好难过。” 他伏在她颈窝叹息,“白英,无论如何,我都放不开你了,你怪我一辈子吧。” 她看着床顶,床顶上绣着两只盘着的龙,重重地压着浅黄的床帐。她想,如果能进来阳光就好了,照在上面,温温暖暖的,会让人觉得是过日子的地方。 她的声音里没有绝望也没有悲伤,只是轻轻地说:“陛下,奴婢没家了。” 窗外残阳铺展开来,艳红旖旎,浅意温柔,他或许并没有懂这句话的意思,只是俯下身轻轻地吻了吻那个小小的人儿,像是个任性只知道讨糖吃的孩子。 她又开始流泪了,安安静静地淌了满脖子,但面上没有悲切,只是怔怔地望着床顶。 她的家没了,这宫里无处可为她家,她若留在这里,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一个能完完整整容纳她的家了。她说的尊卑有别,他永远不会明白。 他略带慌张地擦拭她的眼泪,瘦弱的人儿眼泪不停,面上却牵起了嘴角,说出来的话恍惚有几分温柔,“陛下,若有下次,奴婢的名字就别记得那么清楚了,我们本就陌路,就这样各回各位挺好的。您也别拽奴婢袖子了,您一拽奴婢,奴婢,奴婢就舍不得走了……” 她想着,她这辈子,好像就在遇见他的那一刻幸福了一瞬,此后都在为那瞬幸福埋葬。命里命外,春柳秋华,她还没想明白到底是幸还是不幸,就被时间推了一把,只能跌跌撞撞地接着活下去,甘不甘愿的,只当个糊涂人。 -END- 糟老头坏得很您小小的鼓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~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luofumua.com/lfmgn/964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这才是像样的C语言编程规范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